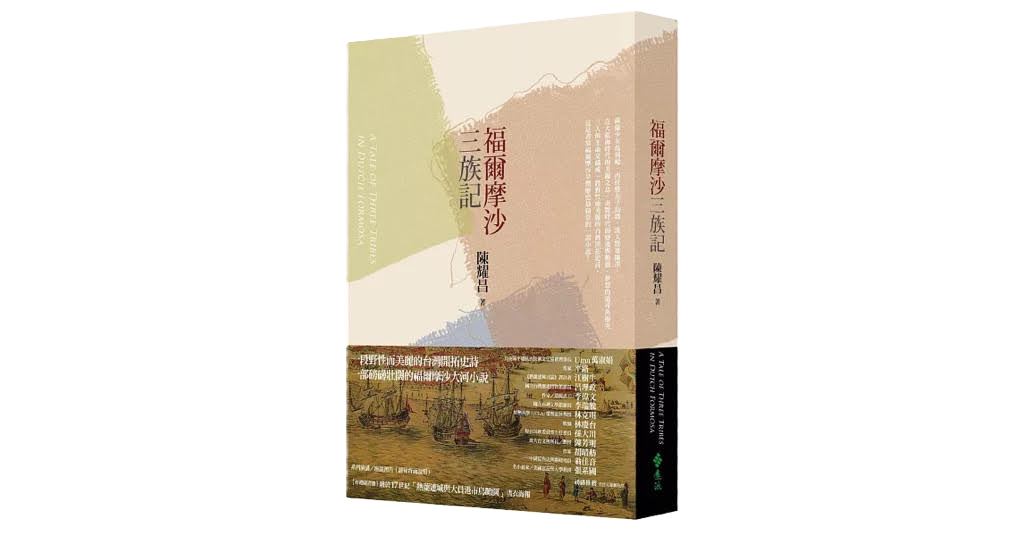陳耀昌
- 本文是陳耀昌醫師著作的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的後記
- 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英文版《A Tale of Three Tribes in Dutch Formosa》的書評:BOOK REVIEW: Pawns in the chess game of history , Taipei Times, May 8, 2025。註:書評的作者是一位在台灣超過20年的荷蘭人,會演布袋戲,中文名羅斌。他一語道破,這種多族群社會的問題就是Identity and Loyalty,這是台灣迄今仍存在的問題。
我寫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,是希望還原台灣開拓史的原貌。
現代一般人講台灣歷史,荷據三十八年幾乎都是一筆帶過,好像一事無成;寫鄭成功驅荷,也是寥寥數語,更把鄭成功寫得像天兵下凡,一戰功成。其實真正歷史不是這樣的。這個現象不是台灣獨有,西方人寫美國史,也往往重英裔五月花號,而輕荷裔新阿姆斯特丹。
從家族溯源開始
我一向遺憾我們家沒有族譜。然而,大約七、八年前,因為掃墓回到府城家鄉,很熱心祠堂事務、七十好幾的叔叔對我說:「我們家的第一代查某祖是一位荷蘭女性。」我大吃一驚,但傾向相信我的家族確實有歐洲人血統。我想,我的鬈髮、濃毛、落腮鬍及爸爸的高大身材,原來其來有自。
第二年清明節再回台南,我向叔叔要求能見證這個第一手資料,因為我渴望知道這位荷蘭女性遠祖的姓名。沒想到叔叔的回答是,他有這樣講過嗎?於是我的尋根心願方見端倪,隨即觸礁,觸發了我寫出「台灣人的荷蘭查某祖的故事」:遙想十七世紀,一個荷蘭少女因父親追求理想,來到當時稱為福爾摩沙的台灣,卻因歷史的偶然、命運的轉折,成了現代某些台灣人的祖先,也順便帶出早期的台灣開拓史。
在書中,我除了虛構以亨布魯克牧師之二女兒瑪利婭來貫穿歷史,其他人物都盡量保持歷史原貌。我希望本書更接近「小說化歷史」,而不只是「歷史小說」。至少大方向是如此。兩位台灣史權威翁佳音教授與江樹生教授應該也有這樣的期許,在此感謝他們逐字讀過,替我修正了許多細節。特別是翁佳音教授,如果沒有他的支持、鼓勵與提供照片,本書不可能完成。
我很幸運,大約自二○○五年開始,市面上出現不少荷蘭時代台灣史的書,更可貴的是江樹生教授譯就的四大冊《熱蘭遮城日誌》,以及《梅氏日記》,讓我驚喜荷蘭人竟然留下那麼多第一手資料。
讀荷據台灣史的結果,我認為,台灣人有荷蘭血統者比我們想像多,而溯其原始有兩個可能性。
一、祖先為荷蘭男性:在荷據早期,荷蘭男性與平埔族女性(西拉雅)結婚者,或不婚而有兒女者,雖不算多,但經三百五、六十年的繁衍,可以變成可觀的數目。而在荷據晚期,因鄭成功來台而來不及逃出的荷蘭男性,有些人往高山逃,於是往北經由諸羅山到鄒族、往南經由打狗而入魯凱及排灣部落。前任荷蘭駐台代表胡浩德(Menno Goedhart)也印證了這個說法。
二、祖先為荷蘭女性:鄭成功來台時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登陸赤崁附近,普羅岷遮城內及散居西拉雅村社的荷蘭人家族有兩、三百人被俘。鄭成功殺了一部分,放了一部分(一六六二年隨船返回巴達維亞),囚了一部分。這些被囚的數十人,到了一六八三年施琅來台後才獲得釋放,回到巴達維亞。其他有數十名荷蘭女性,或為妾、或為奴。見於史者,至少有鄭成功本人和將領馬信娶了荷妾。我相信尚有其他未見於記載者。這些荷蘭女性所生的後裔,大約是鄭氏部隊漢人將領之後。
所以我曾戲說,台灣除了傳統四大族群外,還有「新台灣之子」,包括東南亞新娘所生的第五族群,以及具有荷蘭血統的第六族群;更正確地說,應該是歐洲白人血統,因為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唯才是用、不次擢升,吸引了許多西歐、北歐的有志之士,像十任台灣長官之中,卡隆、揆一都不是荷蘭人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認為,荷蘭東印度公司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雇員來自荷蘭以外的歐洲國家。
因此,台灣的平埔或高山原住民若有西方人血統者,多為男性歐洲人之後;台灣的福佬漢族若具西方血統者,則可能多為女性歐洲人之後,兩者不太相同。
二○○九年四月,我參加荷蘭國慶晚會。令我大為感動的是,荷蘭代表胡浩德夫婦以台灣原住民服裝出場,在場則約有四分之一賓客為原住民;宴會中現烤山豬,跳原住民舞蹈。胡浩德口口聲聲說,台灣原住民是他的親人。甚至當我告訴他「我故鄉在台南」時,他說「Me, too」。而且他說到做到,退休後,他真的定居台南新化,也就是荷蘭時代的新港社。
胡浩德的精神讓我感動。因此,我希望這本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能強調,最早的台灣開拓史是台灣原住民(大洋洲南島語族)、漢人(亞洲黃種人)和歐洲人(白種人)的共同努力。這種三大洲的人種組合,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獨一無二,也就是說,當今仍有不少台灣人身上其實同時流有南方漢人(具百越血緣)、平埔族、再加上歐洲白人的血緣。由人類白血球抗原(HLA)的分析,我估計台灣居民約有一百萬人帶有歐洲白人血緣,雖然純度也許只有一○二四分之一(第十代),甚至四○九六分之一(第十二代)。因此,我寫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,是為了台灣歷史與人類學而寫,不為政治,所以在「楔子」中,我豪情寫下:「為台灣留下歷史,為歷史記下台灣。」
大量爬梳史料為基礎
荷蘭時代台灣史讀多了以後,發現一個大問題: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早期台灣史,不但忽視或抹殺了荷蘭時代的歷史,連明鄭時代的歷史真相也有許多遭到有意無意的掩蓋。荷蘭時代由於當時的大員商館保留了相當詳盡的史料(四大冊的《熱蘭遮城日誌》可為代表),現在還原真相並不算難;另一方面,明鄭時代留下來的史料,如《從征實錄》、《台灣外志》、《海上見聞錄》、《靖海誌》、《台灣鄭氏始末》等等,不但常失之過簡,而且很容易找出錯誤。
另外,明鄭在台二十三年,因為牽涉了不少政治權鬥,有些關鍵事件的真相也被有意掩蓋。鄭氏王朝的兩次王位繼承皆以政變收場,此中必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之事,例如鄭成功是怎麼死的?鄭成功死前是否指定弟弟鄭淼而非兒子鄭經為繼承人?鄭經庶出長子鄭克 的身世為何?如今都是歷史謎團。而明鄭降清以後,清廷的惡意抹殺,幾乎盡毀當時的一切文物,民間也刻意掩蓋;當時的台灣遺民心中自有一個「小警總」。於是迄今不但史料欠缺,真相更是難明。
的身世為何?如今都是歷史謎團。而明鄭降清以後,清廷的惡意抹殺,幾乎盡毀當時的一切文物,民間也刻意掩蓋;當時的台灣遺民心中自有一個「小警總」。於是迄今不但史料欠缺,真相更是難明。
以明鄭時代而言,鄭成功的時代還有楊英《從征實錄》的第一手資料,扼要記載軍中大事,但是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有所出入。到了鄭經時代,留下的記載更是片段及零落。
禮失求諸野,歷史也是。然而如今在台灣民間看到、聽到的明鄭時代事蹟,也都不太可信了。民間傳說的鄭成功相關傳奇,如鶯歌石、劍潭等地,皆非鄭成功蹤跡所到之地。閩南人不論軍民,都喜歡蓋廟,可是三百多年下來,廟方對廟史的傳承常因口述而失真。
台南最具盛名的四草大眾廟就是一例。本來是奉祀當年北線(汕)尾之役打敗紅毛的陳澤,清朝時不敢公然表示是祭祀明鄭「大將」,只好泛說「鎮海大元帥」;不敢說「陳澤」,而改稱「陳酉」。又因同音之故,「大將廟」變成「大眾廟」。其實廟方明示奉祀「鎮海大元帥」,廟內的主神也只有一尊,應叫「大將廟」而非「大眾廟」,其理甚明。根據目前的廟方資料,主神是協助清朝敉平朱一貴事件有功的陳酉。可以說,祭祀的對象由「反清復明」大將陳澤,變為「平定天地會朱一貴之亂有功」的清廷將領陳酉,這簡直是角色錯亂了。在正史中,查無「陳酉」此人;而廟方有關陳酉生平的記載也前後不一,二○○六年版只說是鎮守台南的「提督」;到了二○一一年版,則成了「台灣總兵」、「廣西提督」,明顯是稗官野史之說。
又如,台南市陳德聚堂是陳澤還是陳永華的故居,也曾有過爭議。陳德聚堂奉祀的牌位「永華公諱澤字濯源諡文正」及「洪氏太夫人、一品郭夫人」,明顯是陳永華與陳澤的「合體」,因為陳永華諡號文正,娶洪夫人;而陳澤字濯源,娶郭夫人。我們由陳德聚堂奉祀「開漳聖王」,可以推論這是陳澤故居,因為陳澤是漳州海澄霞寮人士,而陳永華是泉州南安人,陳永華故居不可能會有開漳聖王的記載與遺訓。
所以不論正史、廟宇與民間,對明鄭史料的記載都需要我們努力去發掘與辯證。現在已經不容易,若再繼續以訛傳訛,以後就更困難了。
寫出鄭成功的英雄全貌
鄭成功是台灣史上的英雄,而我希望寫出他的英雄全貌,包括人性的光明面與黑暗面。
在那個明清之際的悲慘時代,不論是君王(崇禎、南明諸王、皇太極、順治)或將領(鄭芝龍、鄭成功、張煌言、李定國、洪承疇、三藩、甚至施琅,以及更早的袁崇煥、滿桂等),每個人都充滿心靈的創傷。因戰火和海禁而流離失所的閩粵百姓就更不用說了。荷治下的福爾摩沙及鄭經西征前的台灣,相對之下反像是人間樂土。
那是一個人人都不快樂的時代,而鄭成功更是一個非常不快樂的英雄。他身世曲折多舛,性格多疑急躁,卻又堅毅不屈、聰明果斷、多才多藝。然而西方的記載把他醜化,東方的論述又把他神化了。於是我們看不到有血有肉的悲劇英雄鄭成功的真面目。
在荷蘭古籍中,鄭成功被描述成毫無人性的暴君。依當時荷蘭劇本記載,牧師亨布魯克未如國姓爺所囑,去向熱蘭遮城守軍勸降,結果國姓爺大怒,連帶處死所有在福爾摩沙的牧師及許多荷蘭人。這個故事廣為散布,更以畫作流傳於世,連台灣人顏水龍顯然都相信了。顏水龍於一九三五年畫的《范無如區訣別圖》,迄今懸掛在赤崁樓的牆上。
然而,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。鄭成功派遣亨布魯克去勸降是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,而亨布魯克等牧師被殺,是九月十二日鄭荷第二次海戰之後的事,中間相隔了四個月。五月二十五日,鄭成功砲轟熱蘭遮城無功而退之後,他對待荷蘭人依然算是寬大的。要等到後來巴達維亞援軍於八月出其不意到來,九月中兩軍第二度大戰,雖然鄭軍慘勝,但死傷甚眾,而且「宣毅前鎮」副將林進紳被荷蘭降兵暗殺,再加上稍早「左前鋒鎮」楊祖和近千士兵被中部的大肚番王所殺,鄭成功懷疑是荷蘭人的煽動,近故加上遠因,鄭成功才大開殺戒。以當時英、荷在南洋各地互相打來打去,這樣的殺戮,老實說,殘忍但非特別過分。只是鄭成功殺害的不是軍隊,而是對福爾摩沙盡心盡力的荷蘭神職人員,因而被渲染了。
相反的,當年不少荷蘭文獻提到,鄭成功處死荷蘭牧師之後,娶了亨布魯克十六歲的小女兒為妾。荷蘭記載說,牧師的小女兒甜美可愛,是眾所公認的美女。這種事在同時代也是不論歐亞多有所聞,不算過分,只顯示出鄭成功平凡人性的一面。但此事竟然完全不見於華文史籍的記載,大概是為了維護鄭成功「治軍嚴明,不擾百姓」的形象,也顯示中國古書「為尊者諱」的偽善。其實這件事還有續篇,依荷蘭人的記載,後來鄭荷訂立和約,鄭成功真的遵守承諾,讓這位荷妾離開台灣。這一點,鄭成功就令人佩服。揆一的後人會來台祭拜國姓爺,豈偶然哉。
剖析英雄之死
最讓我感到有興趣的,是鄭成功之死。
鄭成功死得非常突然,而他的死,影響又非常重大。如果他晚死一年,可能真的會征伐呂宋,也可能後來鄭經沒有機會再統領鄭家軍,則台灣歷史,甚至東亞歷史,勢將重寫。
更奇怪的是鄭成功的死因。綜合民間及官方史冊,鄭成功之死的情節大約如下:
- 《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》:「康熙元年,賊中內亂,成功父子相惡。成功欲殺錦,遣人捕系之,錦稱兵。成功恚甚,得狂疾,索從人配劍,自斫其面死。」
- 《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》:「靖南王耿繼茂疏報:海逆鄭成功因其子鄭錦為各偽鎮所擁立,統兵抗拒,鄭成功不勝忿怒,驟發癲狂,於五月八日,齩指身死。」
- 夏琳《閩海紀要》:「人莫知其病,及疾革,都督洪秉誠調藥以進,成功投之於地……;頓足撫膺,大呼而殂。」
- 劉獻廷《廣陽雜記》:「賜姓之死也,面目皆爪破。曰: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。」
- 梅村野史《鹿樵紀聞》:「面目皆爪破。」
- 江日昇《臺灣外記》的記載最詳細:「五月朔日,成功偶感風寒。但日強起登將臺,持千里鏡,望澎湖有舟來否。初八日,又登臺觀望。回書室冠帶,請太祖祖訓出。禮畢,坐胡床,命左右進酒。折閱一帙,輒飲一杯。至第三帙,嘆曰:『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』!以兩手抓其面而逝。」
- 林時對《荷閘叢談》:「咬盡手指死。」
- 李光地《榕村語錄續集》:傷寒。
- 沈雲《臺灣鄭氏始末》:先說是「病肝急」,再描述黃安勸鄭成功不要為鄭經之事生氣,但「成功益忿怒,狂走。越八日庚辰(初八日),嚙指而卒,年三十有九。」然後,又說馬信也「慟哭不絕死」。
- 徐鼐《小腆紀年》:「金廈諸將拒命,心大恚恨,疾遂革,猶日強起登將台;兩手掩面而逝。」
- 《清史稿》:「狂怒囓指。」
- 楊英的《從征實錄》可信度最高,可惜只寫到該年四月。五月的記載不知是遺失了,還是故意隱而不寫。總之相當詭異。
有關鄭成功之死的過程,不論死於何病,下列的說法是比較一致的:
- 鄭成功大概自農曆五月一日開始不適,在床上躺了幾天。他過世是五月八日,那天的精神體力反而比前幾天好,看起來是病體恢復中,而不像病情加重。
- 鄭成功去世那一天,早上可以長時間坐起來唸明太祖遺訓,可以飲酒,還把屬下奉上的藥丟到地上。也就是說,神智清楚,食慾不錯,而且力氣不小,完全不像重病臥床者之臨終表現。
- 鄭成功去世那幾天,心事重重,非常盼望金、廈有消息來;而對兒子鄭經,既生氣又惦念。
- 鄭成功之死,發生在幾分鐘之內。
- 以他的身體狀況,屬下沒有任何人會想到他那天會過世,但他死前說的話,又很像是遺言。
- 鄭成功死時,馬信在他身旁。鄭成功死後,馬信很快為他覆上紅緞。
迄目前為止,有關鄭成功的死因,現代人的臆測大約有下列幾個病名:肺炎、瘧疾、傷寒、肝炎。當時的台灣是著名的瘴癘之地,所謂「瘴癘」就是瘧疾、登革熱、痢疾、傷寒等傳染病,後人很容易會推測鄭成功死於上述傳染病之一。但以我數十年內科醫師的經驗談,上述說法都不太像,因為最基本的一點,這些細菌、病毒或原蟲所引起的感染,幾乎都會高燒數天,而鄭成功幾乎完全沒有發高燒的記載(「偶感風寒」反而表示不是高燒)。
再深入探討:肺炎的病人大都死於呼吸衰竭,且因為血中氧氣嚴重不足,不可能在臨死當天起床飲酒、讀書、擲碗……等。
瘧疾的病人大都死於貧血、發燒、休克。同樣的,鄭成功死前不像有休克的樣子,也未記載發高燒。
至於傷寒,中醫的傷寒和西醫的傷寒可能不盡相同。登革熱(天狗熱)或痢疾大約可以列入中醫所說的「傷寒」,但鄭成功不見高燒,不見肌肉痛,不見皮膚出血(登革熱),不見腹瀉或血便(痢疾或傷寒),所以通通不像。
而肝炎、急性肝炎的病人,大都死於重度黃疸引發之肝昏迷。鄭成功未有黃疸之記載。同樣的,肝衰竭死者不可能有鄭成功那天早上的種種激情表現。
再則,鄭成功的「直接死因」,見諸文獻的有「抓面而死」、「咬指而死」或「掩面而逝」。然而就醫學觀點,抓面咬指的出血量都不大,絕不致造成休克,如何在數分鐘致死?而且上述的肺炎、瘧疾、肝炎、傷寒,或下述的心肌梗塞、腦中風在瀕死時,也都不太可能做出「抓面」或「咬指」的使力動作。
會在五分鐘內猝死的是心臟病(心肌梗塞)或腦中風。但以鄭成功的年齡及史書的敘述都不像。而且鄭成功死前的言語,像「自國家飄零以來,枕戈泣血十有七年,進退無據,罪案日增;今又屏跡遐荒,遽捐人世。忠孝兩虧,死不瞑目,天乎,天乎!何使孤臣至於此極也!」根本就是在交待遺言。他顯然清楚知道自己將死。心臟病或腦中風而猝死者,不可能在死前那樣長篇大論、激動感嘆,而心臟病死時是胸痛或心痛,會「撫胸而死」,不會「掩面而死」;腦中風的人有一邊身體麻痺,而「掩面」是兩手並用的動作。
所以基本上,我不認為鄭成功死於熱病或感染,或上述任何一種疾病,也不像是心肌梗塞或腦中風。那麼,有其他可能嗎?
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是「自殘」。以鄭成功死前的精神狀況、他的家族史、他的個性、他悲憤自盡,自殘是非常合理的。馬信何以要急急為鄭成功蓋上紅布,顯然為了掩飾血跡及自殘之傷痕。而馬信七天之後亦猝死,太巧合了;更何況,七天,正是閩南人風俗的「頭七」。或說馬信是「慟哭」而死。「慟哭」如何致死?在醫學上也沒有「慟哭致死」這樣的死因。心情悲痛有可能引發心臟疾病或腦中風,但還是這句老話:「未免太巧合了!」所以我高度懷疑,馬信也是步上主子之後路,自殺而死。
如果鄭成功的死因是自殺反而最為合理,也最能解釋鄭成功留下一些類似遺言的記載。
側寫悲劇英雄鄭成功
我想先自鄭成功的精神分析說起。鄭成功有沒有可能自殺?我的另一篇文章〈三太子與鄭成功〉(見本書附錄)提到,祭拜三太子的風氣在台灣比在閩南及大陸遠為盛行,和鄭成功的倡導有關。我去過台灣大大小小祭拜鄭成功的廟宇,廟內都有非常古色古香的三太子神像,而且常常不只一尊,我由此推斷,鄭成功虔信中壇元帥哪吒三太子。鄭成功一方面以哪吒的故事來撫慰自己對生父鄭芝龍的不滿與扞格,一方面也以哪吒的戰神形象鼓勵自己,這也反映了鄭成功的內心衝突和自我矛盾。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哈姆雷特、李爾王、奧塞羅的故事,與鄭成功比起來都差了一級。鄭成功的一生,可說是劇本所創造不出來的悲劇英雄。
我曾和我台大醫學院的學長、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著名的精神醫學教授林克明醫師討論過,他認為鄭成功有希臘神話人物伊底帕斯的「弒父娶母情結」,這個說法我非常贊同。有趣的是,林醫師現在也正寫作以鄭成功為主角的英文小說,請大家拭目以待。
我們的理由是,鄭成功自一歲到七歲是日本人,只有日本人母親撫養。作為父親的鄭芝龍,在這段時間完全缺席。鄭成功七歲以後,被父親接到安海,結果變成鄭成功和母親相處的機會被父親剝奪了。
更糟糕的,來到安海的鄭成功不但未能真正感受父親的疼愛,反因漢語不甚流利、生活不太習慣,受盡叔叔們和堂兄弟的欺凌,讓他更想念在日本的媽媽。所以《台灣外志》說「季父兄弟輩數窘之」,又說他「念母憂思,夜必翹首東向」。那時,長輩比較欣賞他、照顧他的,大概只有較具文人素養的四叔鄭鴻逵;平輩與他較交好者,可能是族兄鄭泰和幼弟鄭淼。
鄭芝龍自然極疼愛鄭成功,但他給鄭成功的父愛不是家庭生活方面,而是聘名師、上太學、布人脈,包括十五歲就為他找個同鄉惠安的最高名門、「禮部侍郎」董颺先之姪女為妻。鄭芝龍對鄭成功「望子成龍式」養成教育的影響當然很大、也很正面,然而我們也可以想見,鄭芝龍對兒子必會因「責之切」,偶爾有一些過度的要求。林林總總,小鄭森(那時還不叫鄭成功)的幼年生活顯然是不快樂的,心裡對父親可能是怨多於愛的。而且偏偏鄭芝龍後來沒有走正路,所以鄭成功和父親的舊心結和新理念的衝突就一起浮現。
是巧合或是必然,到了後來,鄭鴻逵、鄭成功、鄭泰及鄭淼都沒有隨鄭芝龍投降清廷。也許是鄭成功對鄭芝龍所產生的不滿,加上少年時代所受的孔孟教育,以及一半日本人血統產生的忠君思想,讓他對清廷的態度與父親鄭芝龍做了不同的選擇,也就踏上「忠孝不兩全」之路。於是,鄭成功以「三太子哪吒」自喻,也以戰無不勝的「中壇元帥」自勵。
如果像《封神榜》裡,哪吒並不影響父親李天王的功名也就算了,鄭成功和父親分道揚鑣,卻導致父親及弟弟的被囚、被殺,結果,一六四六年鄭成功因父親降清而決裂的理直氣壯,竟變為一六六二年鄭成功對父親被處死的滿心歉疚。他聽到父親被處死的訊息後,口頭上不相信,卻半夜起來痛哭。這也像伊底帕斯的故事一樣。希臘神話中,後來當上底比斯王的伊底帕斯知道自己在不知情中弒父娶母之後,內心充滿了悔恨與罪惡感,竟然自挖雙眼、放棄王位,到處流浪。
鄭成功的終局
鄭成功比伊底帕斯更不幸。一六六二年二月底,他接到父親因自己而死的死訊,五月底或六月初接到永曆帝的死訊(之前他一直被張煌言痛罵勤王不力),然後又面臨自己和兒子鄭經決裂的空前危機與羞辱(鄭成功心裡可能有現世報的感覺),於是因心裡壓力太大而自盡,是一個很合理的推測。也唯有如此,才能解釋鄭成功的猝死,以及史籍所說的掩面而死、抓面而死等,甚至包括馬信必須以紅緞蓋住鄭成功的遺體。
鄭成功以三十九歲之齡過世,絕非福壽雙全,以漳泉人士的習俗,不會用代表喜慶的紅緞去覆蓋,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為了掩飾他因自殺而噴出來的血跡。而掩面而死、抓面而死,再加上鄭成功死前說的「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」,顯示傷口應該在臉部。「齩指身死」應是掩飾之詞。這些都說明了馬信何以要用紅緞覆蓋遺體。
所以我認為,鄭成功不是一般人以刀劍自盡的「自刎頸項」(通常只有一刀),而是在極端衝動之下,自殘式地亂刀刺臉(常有好幾刀,等於是以刀毀容,傷口常多而深,自然出血極多,導致迅死),所以說「面目皆爪破」。
那麼,何以要掩飾鄭成功是自殺?我想,於大局、於私人都有理由。於大局而言,我認為鄭成功的自殺很可能僅留有遺言,未有遺書。即使留有遺書,也會引起真偽之爭。如果率爾宣布鄭成功是自殺,必然無法取信於台灣及金廈之所有將士,徒生風波。加上台灣初定,世子鄭經不但不在台灣,還率重兵耆臣與父親隔海對立。且不論鄭成功是否留下文字要廢鄭經或立鄭淼,都會使局面更為複雜難解,甚至雙方惡戰對決難免。
再說,鄭成功人生的最後一刻,情緒顯然非常激動,這讓馬信等人認為,鄭成功之自殺不是光彩或莊嚴的死法。現實的考量加上傳統觀念的「為尊者諱」,就沒有把國姓爺的死亡真相公諸於世,成了歷史永遠的黑幕或謎團。
然而,歷史是吊詭的。鄭成功自覺屈辱而死,但在後世的眼光看來,他雖死有遺憾,但不僅是「民族英雄」、是「創格完人」,而且已把「缺憾還諸天地」。
鄭成功之死因將永遠無法有定論,而我以醫者之專業知識,試著去解開這個謎團。如果是錯誤推理,還請國姓爺原諒;如果幸而言中,不知國姓爺在天上是高興「真相大白於世」,還是大怒「小子洩漏機密」?但至少我們可以斷言,即使國姓爺是自殘而死,也絲毫不會損及他的歷史定位與後人的追思景仰。